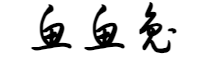他的作品虽然持有反叛且顽固的政治态度,但是他也以温和的幽默感闻名。理查德·布兰科曾经评价道:“埃斯帕达的诗作持续地将诗人定义为‘情感的历史学家’。与惠特曼一样,埃斯帕达在我们心中激荡起一种无法被否认的社会意识及联结。——芝加哥诗歌协会(Poetry Foundation)
||||
2018年5月,美国诗人马丁·埃斯帕达(Martín Espada)获得罗斯利里诗歌奖(Ruth Lilly Poetry Prize),该奖项由美国芝加哥诗歌协会(Poetry Foundation)设立于1968年,每年颁发一次,旨在奖励终身对诗歌写作有突出贡献和成就的美国诗人,是美国最为杰出的诗歌奖项之一。往年获奖者有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威廉·默温(W.S. Merwin)、理查德·韦伯尔(Richard Wilbur)、乔伊·哈卓尔(Joy Harjo)等。
美国诗人马丁·埃斯帕达(Martín Espada)获得2018年的罗斯利里诗歌奖
马丁·埃斯帕达是波多黎各裔美国诗人,出生于1957年,他主要围绕美国波多黎各移民的主题创作揭示拉丁裔美国人的政治诉求、移民生活、及社会现实的诗歌。曾出版《反叛是爱人手中的圆》(Rebellion is the Circle of a Lover's Hands),《咳嗽与死亡暖气机之城》(City of Coughing and Dead Radiators),《流放了他们的岛屿上传来小号声》(Trumpets from the Islands of Their Eviction),及散文集《反抗者的爱人也是反抗者》(The Lover of a Subversive is Also a Subversive: Essays and Commentaries)。
埃斯帕达诗集《反叛是爱人手中的圆》(Rebellion is the Circle of a Lover's Hands)
2001年,埃斯帕达入选美国桂冠诗人,其作品曾先后入围普利策奖、国家书评人奖,并获得罗伯特·克里利奖(Robert Creeley Award)、美国图书奖(American Book Award)、罗斯利里诗歌奖(The Ruth Lilly Poetry Prize )等著名文学奖项。
他的语言以高强度的紧张感、真挚而一针见血的洞见,书写着多元化的人物的心声,《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撰文评论称:“马丁·埃斯帕达的作品定义了世纪之交的政治诗学。”
埃斯帕达:“即使是最政治化的诗歌都是一种信仰的行为”
埃斯帕达谈诗与历史的包袱
——Steven Ratiner(以下简称SR)对 埃斯帕达(以下简称ME)的采访
SR:您曾说过,“诗人的职责之一就是要挑战“官方权威的历史”。而您也在写作中践行着这一观念:您的诗歌里不乏对那些不曾为历史和社会所知的英雄的赞美与颂扬。《克莱门特的子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ME:是的。克莱门特·索托·费雷兹(Clemente Soto Vélez)是因某些刻意的缘由而被这个国家忽略的英雄。您不妨想想诗歌中所谈及的有关他的事迹:他曾于整整六年间辗转于各州禁狱——就因为他为波多黎各的独立发声、思考、写作。当时,波多黎各正处于第一修正案(其核心为言论自由)艰难行进的历史进程中。所以克莱门特被关进了监狱。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狱中经历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使我们变得尖刻、痛苦,并走向自我毁灭。但是,克莱门特却并未如此:他成为了纽约-波多黎各文学协会的创立者。他是一名组织者,一位记者,一个86岁却依旧在奋斗的人。一个无以伦比的人。所以,是的,当我在写《克莱门特》这首诗的时候,我正尝试重新定义“英雄”与“英雄主义”。
波多黎各诗人克莱门特·索托·费雷兹
SR:您刚刚所表达的是一种强势、明确的政治观念。但我非常欣赏您的诗歌恰恰是因为这种咄咄逼人的声音的缺席。我记得您的诗作《两个墨西哥人于1877年5月3日在圣克鲁兹被处死》所围绕的是一张老照片。这首诗并没有明显的批判意味,看上去它似乎仅仅是在为读者描绘与展现一个冰冷的经验事实。
ME:首先我想说明的是,于创造者而言,“描绘”和“叙述”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如果我的作品是基于某一个景象,那么它就会围绕这一景象,对其进行描绘,而这也就足够了。当然,当你读到那首诗的结尾,你就会发现我其实也在描述那些被处刑的人的面庞,描绘他们彼此之前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这里非常明显地表达了对于他们的共同特性(即“墨西哥人”)的谴责。
最终一切只剩下绞刑队伍的面孔
他们像被铸在1877年硬币上
在历史里磨灭
他们中,有人依稀看着处决现场
露出惊恐的神情,
一个穿高领衬衫的男孩得意地笑着
还有些人在礼帽檐的阴影下注视着
但他们这群人,全被拍进了照片中
——马丁·埃斯帕达《两个墨西哥人于1877年5月3日在圣克鲁兹被处死》
我知道政治诗歌不好写,有很多“陷阱”... 但是,这首诗中所描写的并不是被人叙述过的历史。人们通常都不知道,不仅仅是黑人,奇卡诺人也曾在美国西南部以惊人的数量被大规模地屠杀。而这在当时,却是一种稳固政权的重要方式。所以,当人们讨论西部如何赢得政权的时候,也不能不讨论这一部分被隐藏的事实。
早年奉行极端白人中心主义的圣克鲁兹地区
SR:第二个贯穿您所有诗歌的重要母题是愤怒。如同低音音符一般,愤怒流演在您的全部诗作之中。毫无疑问,在我们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愤怒是禁忌——连感受愤怒都是不被允许的,更别说表达愤怒了。但是,我觉得,您在诗歌中大量地表达和凸显这种愤怒的情绪,会产生一种危险:所有的愤怒最终将会在诗歌中揉合并融为一声怒吼。
ME: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让愤怒成为一首诗或者一组诗的主导,的确可能使读者除了愤怒之外接收不到任何其他的情绪或信息。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通过对语调的选择来避免,也就是说,只要在诗歌中变换语调,愤怒可以成为诗歌中一种持续的能量。与“愤怒”这一低音相并行,我在诗歌中也同时演奏了许多不同的音调。如果您翻阅了这本诗集,就会发现这一点:《两个墨西哥人》是语词异常尖刻的一首,但是在《革命性西班牙课程》或《英语高中的浴室新政》中,唯一的“锐刺”就是一点儿幽默感。愤怒是这些诗歌共同的主题,然而它在诗歌中的表达和展演却截然不同——因为它们所采用的语调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刻意的选择,为的是能够呈现多元的样态。
英语高中的浴室新政
厕所里
男孩们用西班牙语轻声聊天
办公椅上
校长在隔墙细听
他只能听懂一个词
那是他自己的名字
而这使他便秘发作
于是他决定
禁止西班牙语
从厕所开始
现在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奕奕 译
The New Bathroom Policy at English High School
Martin Espada
The boys chatter Spanish
from the bathroom
while the principal
listens from his stall
The only word he recognizes
is his own name
and this constipates him
So he decides
to ban Spanish
from the bathrooms
Now he can relax
在美国的殖民历史上,政府一直坚持推行“只准说英语”的语言运动(English-only movement)
SR:您的诗歌在某些层面会让我想起肯尼斯·帕钦(Kenneth Patchen)的作品。他同样也运用了幽默和讽刺来构写其社会评论和反战诗歌。而这给我们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去观视自己的生活经验。
ME:顺带说一句:我不得不承认,愤怒是我们“不应该有”的一种情绪,因为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来说,如果你开始审视为什么自己会产生这样的愤怒,你也就会开始追证这究竟是谁的责任——而这可能会导致对现状的冲击与挑战。所以,在压制愤怒这一举动背后,存在着某些政治动因。
SR:然而,您似乎是有意识地将这种愤怒的情绪传达在诗歌中,并将其转化成其他事物——一部分是为了自我救赎,但另一部分也是为了艺术本身。
ME:这么说吧,许多人和我一样,有着类似的经历,思考着相同的话语,但从来没有机会去发声和表达,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机会去写诗、发表、并朗读给听众们。而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作为诗人的责任——去为那些没有机会表达的人而发声。而这就是“发声之诗”(poetry of advocacy)。
SR:这就涉及到您诗歌第三个重要的方面——一种超然之感,一种能够引领我们超越个人的苦痛磨砺和历史负担的事物——而这常常与家庭相联结,与最深层次的人类关系中所可能产生的救赎有关。
ME: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和个人经验都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在压制与反抗、施害者与被害者之中存在着一种动态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挣扎和斗争,也有胜利。所以,我想要在诗歌中到达那里——那种动态的张力和冲突,所有的事物于一处汇合、冲击、燃烧。对我来说,尊严、反抗、坚韧、团结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感情的表达,都植根于家庭之中。
SR:您的《布韦那文图拉·罗伊格的探戈舞曲》(La Tumba de Buenaventura Roig)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首诗中,您与父亲一同重回波多黎各,找寻您曾祖父的坟墓。
ME:首先,讽刺的是,在诗的最后我们并没有找到那座坟墓。但我们确实收集到了许多关于我曾祖父存在的痕迹。在旅途中,你最终所发现的,并不总是你所计划要找寻的。这首诗不仅仅关乎布韦那文图拉·罗伊格,也关乎他那个年代的波多黎各——那时,波多黎各是一个即艰难困苦又异常美丽的地方,一个如今不再存在的地方。所以,这首诗中一直贯穿着一种强烈深邃的归属感,而它是大于我作为个体本身的。正如我在最后一个诗节中所说:
我们在群山面前是如此渺小
而我们倾听你的声音
在五百年来农民的和声中
有一首野性的神圣的歌
像暴雨一样来临
——马丁·埃斯帕达《布韦那文图拉·罗伊格的探戈舞曲》
我仿佛身临那一时代,而这是一种异常激荡的感觉。因为尽管那时我们的认知还非常有限,我们也已经开始了解到自己其实属于某种更大的图景之中——当我们被召唤着做出下一个决定的时候,这就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波多黎各圣胡安的海边墓地
SR:这让我想起了诗集中我最喜欢的一首诗 《Colibr'i》。这首诗里描绘了这样一个可感的时刻:家庭和爱的联结与个体的痛苦和历史的重压相抗衡。
ME:这首诗的灵感直接来源于我与妻子度蜜月时的一段经历。我们当时在哈尤亞(Jayuya)的老式庄园留宿,那里只供应最简单的粗茶淡饭......但却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某天,我们从房间里走出来,发现一只蜂鸟被困在走廊里。那只鸟如同发了疯一般,猛烈地撞墙,想要逃出去——不难看出,它是一只野鸟。见到此情此景,我的妻子发自本能地去安抚这只鸟:她用双手环绕着它,想要捧着它!你可以想象,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当她在尝试抱起那只小鸟时,我推开了窗户的木遮板,我妻子猛地将小鸟抛向窗外,这只鸟就这样消失在薄暮之中。
对我来说,这整个场景近乎神迹一般。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为此写一首诗,但我花了很长时间将它安置在一个合适的语境中,即在当地游荡的魂灵。距离那个庄园约15分钟的路程有一个叫做"la piedre escrita"的地方,字面意思就是“被刻写的石头”。在这个地方,你能够看到当时被西班牙人征服并驱走的泰诺族(Ta'ino)印第安人们留下的石雕。在占领了泰诺族之后,西班牙人使用剑、大炮等武器屠杀这些印第安人,同时抹去了他们留有的全部文化、语言和习俗,将一切重新命名。所以,在我这本诗集中,一个重要的母题其实是命名的权力:谁能够命名你的经历?是你自己,还是别人命名并强加于你?所以这首诗想要探讨的是占领之后所遗留下来的东西。诗的结尾是一段对我妻子的赞歌,但它同时也是对所有善良的人的歌颂,并寄予了这个世界也能如此运行的期望。
在哈尤亞地区的“被刻写的石头”
SR:但您所要传达的仅仅是期望吗?难道您不是在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修复个人和历史所带来的创伤,就像您和妻子所做的那样——不仅仅是安抚那只鸟,并且还要重新给予它自由?
ME:我之所以会有期望,是因为那些善良的人依旧存在。无论如何,我们依旧是人类,依旧能够保有关爱、良善、慷慨之心。尽管纵观历史中所发生的各色残忍而黑暗的事情,我们的确不该对人们能拥有善良、慷慨这些品质抱有幻想。但是,他们的确存在。
采访编译材料:"Poetry and the Burden of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Martin Espada."(丛琪 编译)
2017年9月,台风袭击后的海边墓地
布韦那文图拉·罗伊格的探戈舞曲
致我1941年逝去的曾祖父
布韦那文图拉·罗伊格,
千万人曾聚在山坡上
看你葬礼当天出现的
伟大月食。
现在,你的骨肉已随
陡峭山岩上的草木
像海浪一样归去
遗漏在荆棘丛中
野草在太阳下如
切甘蔗的人般弯腰受苦
喝醉了的守墓人找不到
你的坟墓
眯着眼睛寻找你的名字
吐着口水,步履蹒跚
白色的基督圣像高举双手
播下像庄稼一样的白色十字架
布韦那文图拉·罗伊格,
你在乌图阿多建起了一座石桥
多年以后被河流冲垮
河水咆哮,仿若被遗忘的神
你的脸颊上汗流涔涔
夹杂着咖啡豆的烟尘
你的侄子长眠于
家族的玉米地下
一场暴雨溺毙了所有
他的血像凤凰花一样沾在
自杀的白衬衣上
布韦那文图拉·罗伊格,
在你是镇长的那个小镇
广场上曾有一条长凳
镌刻着你家族的姓名
在叛军入侵的时候
他们踏着整齐步履
如甘蔗田般静
你号令乡民组成队伍
他们戴着干草帽
他们的背脊,只背过
庄稼和新宰的牲畜
布韦那文图拉·罗伊格,
你负担不起昂贵的耶稣圣像
现在连最老的挖墓人
都找不到你了
他有一个英式的姓
他的祖先是来自英格兰的海盗
他从口袋里随手拿出一根烟
搜寻关于你的葬礼的记忆
远处有一辆货车在行驶
仿佛多年前的沧桑
慢慢地使他眼睛周围的皮肤沦陷
在五百年来农民的和声中
泼洒在墓地的废墟上
在小镇的广场和教堂上
而圣米格尔的雕像
仍能用他的铁链
勒死恶魔
奕奕 译
La Tumba de Buenaventura Roig
for my great-grandfather, died 1941
Buenaventura Roig,
once peasants in the thousands
streamed down hillsides
to witness the great eclipse
of your funeral.
Now your bones have drifted
with the tide of steep grass,
sunken in the chaos of weeds
bent and suffering
like canecutters in the sun.
The drunken caretaker
cannot find the grave,
squinting at your name,
spitting as he stumbles
between the white Christs
with hands raised
sowing their field
of white crosses.
Buenaventura Roig,
in Utuado you built the stone bridge
crushed years later by a river
raving like a forgotten god;
here sweat streaked your face
with the soil of coffee,
the ground where your nephew slept
while rain ruined the family crop,
and his blood flowered like flamboyán
on the white suit of his suicide.
Buenaventura Roig,
in the town plaza where you were mayor,
where there once was a bench
with the family name,
you shouted subversion
against occupation armies and sugarcane-patrones
to the jíbaros who swayed
in their bristling dry thicket of straw hats,
who knew bundles and sacks
loaded on the fly-bitten beast
of a man’s back.
Buenaventura Roig,
not enough money for a white Christ,
lost now even to the oldest gravedigger,
the one with an English name
descended from the pirates of the coast,
who grabs for a shirt-pocket cigarette
as he remembers your funeral,
a caravan trailing in the distance
of the many years
that cracked the skin around his eyes.
Buenaventura Roig,
we are small among mountains,
and we listen for your voice
in the peasant chorus of five centuries,
waiting for the cloudburst of wild sacred song,
pouring over the crypt-wreckage of graveyard,
over the plaza and the church
where the statue of San Miguel
still chokes the devil with a chain.
题图:Alex Webb and Rebecca Norris Webb: Slant Rhymes.
#飞地策划整理,转载提前告知#
首发于飞地APP,更多内容请移步飞地APP
投稿邮箱:contribution@enclavelit.com
策划 / 编译:奕奕、丛琪、歪歪 | 编辑:一颗